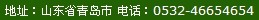|
一、地域社会中的八省客长 八省客长是八省各个会馆的“出省”(代表之意)客长,其在地方权力网络中的地位变化实质上反映了八省会馆的地位变化。关于八省客长与八省会馆的关系,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八省客长汤廷玉、童潞贤等人在给县令的一份“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说明: 窃思八省客长设自雍正年间渝城遭乱之后,人民稀少,渐有各省人民来此商贾,日久寄居,遂有交涉事件,以各省风气不同,致多杆(扞)格。虽有司驾驭,究难洞悉民隐。是以乾隆年间,各省先后设立会馆,渝城遂为客帮码头,疏通商情,始有八省会馆首事名目。选派各省中老成公正、名望素孚之人公举充当,有事□出,妥为调停,以安商旅。 上引材料至少说明了四个问题:一是在清初重庆地方社会重建过程中,有大量的外省籍商民来到重庆;二是八省客长(八省会馆)出现的时间,应该在乾隆初期,因现在《巴县档案》保存资料的限制,我们还无法获知八省会馆创办之初的情况;三是八省客长设置的目的源于当时各省商民之间纠纷不断,而地方官员又难以解决,需要八省客长来进行协助,这也说明八省客长最初的影响仅在外省籍的商民之间;四是八省客长与八省会馆的关系,八省客长是八省各个会馆的首事,每省一个“出省”客长,组成八省客长。 关于八省会馆的创建过程,因笔者有另文叙述,此不赘述。一般来说,会馆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先设会,募集资金,再买房产、置田产收租,这样一个逐渐实体化的过程。 下面是巴县八省会馆的一个简单情况。 表一巴县八省会馆所祀神祗及具体位置表: 省别 所祭神祗 庙名 位置 备考 湖广 大禹 禹王庙 东水门内黉学街 广东 惠能 南华宫 下黉学街 陕西 关帝 三元庙 朝天门内三元庙 毁于年“九二火灾” 山西 关帝 关帝庙 都邮街上街 福建 妈祖 天后宫 朝天门内 毁于年“九二火灾” 浙江 伍员 列圣宫 储奇门内三牌坊西北侧 重庆市食品公司车队 江南 准提 准提庵 东水门内 今重庆市物资局仓库 江西 许真君 万寿宫 陕西街东侧坎下 毁于年“九二火灾 资料来源:民国《巴县志》卷二《建置?庙宇表》及彭伯通:《重庆的“八省会馆”》,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巴南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巴南文史资料》第13辑,年。 清代的重庆以大梁子为界分为上下半城,下半城靠近长江边,最主要的商业街有陕西街、白象街、新丰街、上下都邮街、新街口、县庙街、三牌坊。《重庆乡土志》称:“大宗商业都集于下半城,上半城不过零售分销小本贸易及住居宅院而已。”上表所列的八省各个会馆全都在下半城靠长江沿岸。这从一个层面显示了八省会馆与重庆商业之间的紧密联系。 到了清代中期,八省客长逐渐在巴县地域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窦季良的研究,在清代咸同之际,重庆的八省客长除举办着若干同乡互助的事业之外,还在地方办理厘金、积谷、保甲、团练、城防、慈善等地方公共事业,成为地方社区建设的中心。 咸丰九年(),云南人李永和、蓝大顺率义军从由川南入四川,全川震动。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八省客长汤廷玉、童潞贤等人在给县令的一份“禀”文中谈及了此一事件对八省客长在重庆地方社会中所起的作用: 自咸丰发匪入川,商民思患预防,经八省绅商筹议禀明前宪,始设两局厘金,商捐商办。进关老厘咨部申解,出关新厘留渝就地办公,以供保甲团练之费,所以厘金保甲各局皆有八省经手事件。 八省客长在咸丰以后逐渐掌握了重庆的厘金局、保甲局的控制权。言外之意,重庆的地方财政中的大部分收入和主管地方安全的机构的领导权都在八省客长的手中。同样,光绪十一年巴县的一份“札”文中也称,“照得渝城各局公事,向委八省首士经管,一经承办,责任匪轻”。 与掌控重庆的治安、税收同步,八省客长通过办理善堂,也进入到了重庆地方社会的救济网络之中。 二、至善堂概述 经过明清之际长达四十多年的战争破坏,巴县原有的善堂早已荡然无存。清平定四川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各类善堂仍没有得到恢复。随着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恢复,以及清政府在政策上的鼓励支持,巴县的各类善堂在乾隆年间开始建设起来,虽时有兴废,但兴办之举却一直传承下来。民国《巴县志》称:“巴县为通商大埠,陶朱、猗顿时有其人,富而好行其德者,尤多有之,治城之内,善举迭兴。” 巴县善堂的兴办,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是乾隆年间。乾隆二年(),清政府规定:“各州县设立养济院……令各保甲,将实在孤苦无依者,开明里甲年貌,取具邻佑保结,呈报州县官。”这种由官方出资,收养孤苦无依老人的福利机构,由于清政府的重视,在全国各州县逐次建立起来。乾隆三年(),巴县知县王裕疆创办养济院,该院建于佛图关后石马槽,院址系民妇张沈氏捐献。经费来源分两类,一为地丁银内支销,所拨经费收养孤寡老人92名;另一为商捐。赡养的老人最初为33名,后增加到86名。院内孤贫老人每日给银一分。从经费来源看,巴县的养济院并非完全按清政府的“制度”办事,从一开始便有商人的因素在内。 除了官办的善堂外,这一时期,民间力量也开始兴建善堂,兴办者主要是一些外来移民。如乾隆十八年(),移民汪子玉、樊佑周、李学易等十二人创立敦义堂,共捐银二千八百多两在朝天观买房收息,“每年约收租银一百四十两,以所入购本置棺”。邑人周开丰在《敦义堂施榇碑记》对该堂兴起的过程及发起者的情况有简单的记载: 夫生有所养,死有所归,此人情之大凡也。而胳为之掩,骴为之埋,尤仁政之急务。乃人之困极无告者,其生也已无所养,又安望其死有所归?是以好义行仁者,恒怀恻隐,生则有药饵之施,死即有棺槥之恤。……吾郡地当孔道,人满堪忧,而其中有所谓困极无告、死无所归者,更累累不乏。于是两江、秦、楚及吾乡乐善义士某某等同心翕虑,为施榇之举于朝天观内建敦义堂,鸩工治器,务求坚整。有羁孤病死者,坊邻来告,察实便给行之。数年所济多多矣。今复虞所暨者寡而力薄不能持久也,每人更捐泉布,力裕者二十缗,次或十五缗、十二三缗,以至四五缗,不以数拘,各随其量。聚而出贷于人,照例取息,以备工料。并置市廑一区,防其不继。 可以看到,敦义堂的发起者主要为江南省、山西及湖南省的移民,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有很多移民来川之后,“羁孤病死”而抛尸荒野。从敦义堂的发起者身份来看,主要是个人行为。道咸以后,乾隆年间所办的善堂,无论官办或私营,都因为年久弊生,“值年舞弊侵蚀”,堂下所属产业消亡殆尽,善业不举。 道咸以后,巴县的善堂进入到了第二个时期。此一时期的善堂创办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数量较多。据笔者对民国《巴县志》的统计,道光以后至光绪中期,至少兴办体心堂、尊德堂等善堂九所。下面是这九个善堂的一些简单情况。 表二巴县善堂简表 善堂名 发起者 成立时间 岁入(单位:元) 岁支(单位:元) 地点 体心堂 县人宋国符等 道光二十四年() 余 余 南纪门内天街 存心堂 县人傅中和等 道光二十四年() 铜鼓台街 至善堂 绅民雷晋廷等 咸丰九年() 瓷器街 保节堂 官办,后托至善堂代管 同治五年() 培善堂 绅商某等 光绪四年() 租谷七十余石 鹅颈岭 义济堂 绅商 光绪十七年() 金紫门顺城街 尊德堂 周伯阳等 光绪二十四年() 余 余 南岸海棠溪 崇善堂 商民胡宝华,同知袁培铣(均为湖北黄州人) 光绪三年() 善款随募随销,焚献灯油香烛薪工食费等项共钱一百八十钏 金沙坊 普善堂 绅商王钧、雷德庸 年 共支发钱二千四百九十六千 东水坊石门坎 资料来源:民国《巴县志》卷十七《自治?慈善》;《巴县档案》6-6-。 第二个共同特征是这些善堂主要由商人捐资兴建,由“人民自行筹措,不受官司挹注而成”。这与清代重庆繁荣的经济有密切关系。在重庆所有的绅办善堂中,至善堂的名声最响,实力最为雄厚,“善款视他堂为多”。 至善堂创立于咸丰九年()五月,由八省会馆创办,最初仅有医馆、义塾,并开展收字纸、捡白骨、施茶水等慈善活动。至善堂创立初期,由于资金有限,还没购买相关的地基、房屋,办公场所都是临时租借,“所设义学、医馆尚属租地”,掩埋弃尸所用的棺板也是寄放在各庙之中,由寺院代为保管。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至善堂的救济活动。如寄放在寺庙中的棺板由于照顾不周,雨淋日晒,常发生被损坏的事情。此后,至善堂每年都向各商号募化,筹集资金,购买办公用的房产、埋葬的义地,以及用来放佃收租的田产。至同治四年始建为堂。 由于八省客长拥有较为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其他善堂相比,至善堂的堂产一直处于递增的过程。到光绪三十四年(),至善堂就房产来说在城内已经有杨柳坊老街、官井巷、南纪坊、南清水溪善庄及城外南岸崇文场数处。 下面根据成书于民国初年的《至善堂材料汇编》与年《重庆市至善堂造具市区财产目录清册》来看该善堂堂产的形成过程。 表三至善堂房产形成过程表 时间 过程 堂产价值 用途 同治二年 买杨柳坊曹忠信的房屋一院 银两 至善堂办公用房 同治四年 首士蒙应志堂将其所买孝里一甲海棠溪田土两块捐给至善堂 义冢用地 同治五年 贡生刘价夫、监生刘树芬各捐地名唐家沱附近的田地一块 义冢用地 同治五年 买丰碑街李沈氏房产一处 银40两 同治六年 买官井巷三义和房屋一院 银两 同治六年 买张九成田产若干 银两 光绪五年 买官井巷杜吴氏房屋一院 银两 光绪八年 厚磁街李王氏房产一处 银两 光绪十一年 买白象街朱祥麟房产一处 银两 光绪十二年 买张吉福堂房产一处 银两 光绪廿三年 买花街子街李双和堂房产一处 银80两 光绪廿五年 买药王庙街吴氏房产一处 银两 光绪廿八年 买林森路张成之房产一处 银两 光绪三十一年 中兴路吴瑞林房产一处 银两 光绪三十三年 买老磁器街四知堂房屋 银92两 民国三年 林森路李伯卿房产一处 银两 民国十年 老街向春舫房产一处 银两 资料来源:民国《巴县县署》档案-1-《至善堂材料汇编》及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至善堂造具市区财产目录清册》。 上表主要为至善堂堂产中有关房产部分,至于田产部分方面,《重庆市至善堂造具市区财产目录清册》中也有大量记载,因原始材料并未提供购买的时间和所花费的银两,这里就不一一列出。 到同治年间,至善堂已是巴县规模最大的善堂机构了。同治四年东城京畿道监察御史、吏科给事中伍辅祥在《至善堂诸善举序》中对该堂的筹办及规模有高度的评价,他说:“夫斯堂之创始仅数年耳,而规模宏大。” 同时,同治五年(),受知县黄朴委托管理保节堂。保节堂原为官办善堂,后因管理不善,经费不敷使用,交给至善堂代为托管,当时资产共有两白银。光绪九年(),为了弥补保节堂接济节妇的额数太少的缺陷,添办全节堂,新增受济节妇五十三名。 前已论及,至善堂由八省会馆所创办,此一局面一直延续到民国后期。这也得到档案资料的证实。下面我们来看光绪三十四年()左右,至善堂各首事的个人情况及其与八省客长的关系。 表四至善堂各堂首事简表 年签轮管 名 衔 籍贯 名 衔 籍贯 至善堂首事 申迪纯 四品衔州同 贵州 邵永珍 同知 浙江 朱平祯 四品衔同知 江南 陈继先 监生 湖北 学堂首事 陈崇功 廪生 巴县 朱蕴章 廪生 巴县 医馆首事 赵学坤 监生 湖北 周泽先 从九 湖北 养瞽首事 罗亨谦 附生 巴县 郭义 监生 巴县 孤孀首事 赵城璧 同知 湖北 申大道 监生 广东 全节堂首事 何士瑞 监生 湖北 吴骏英 廪生 巴县 卢宏政 附贡 巴县 萧鼎光 监生 江西 保节堂首事 黄金海 四品□职 江西 胡代谦 监生 湖北 资料来源:巴县档案6-6--19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到,至善堂四首事籍贯全为外省人,申迪纯等人同时也是八省客长,而至善堂所属各堂,大部分仍由移民及其后裔充任。至善堂一直坚持民捐民办的原则,首事每年公签轮换。 随着慈善活动的扩展,至善堂的自身内部的管理体系也逐渐完善起来。同治四年(),川东道道台恒保在给至善堂首事雷晋廷等人关于立碑存照的请示中,批示“查该绅等利济为怀,广行善事,并创建善堂,以为公所,询属可嘉之至,准其如禀立案。嗣后,该绅等尤当尽心经理,俾各善事有加无已,济世利民,永垂久远”。至善堂创堂之初,就设立严格的堂规,以期堂务久远。“善款多,则眉目宜清,免日久挪移,致混乱也;堂务繁,则责成宜分,免致彼此推卸,致废弛也”。 在《巴县档案》里保留了大量详细的关于该堂进行规章建设的内容。下面,我们以相关的记载为依据,对该堂的规章进行粗浅的分析。 首先关于善堂的日常管理,该堂规定,所请看司每天要把堂内打扫洁净,不准在堂赌博、演戏及容留陌生人入住,亦不准妇女入内;其次,该堂每年选举总理一人,协办三人,管理银钱帐目,及登记造册本年所做善事;第三,此时堂内无底金,还靠募集来置产生息,所以各在堂办事之人,不设伙食。同时也要求各首事实心办理,不得擅专、矫功;每年春秋两季各请客一次,感谢各善主的善意。该堂对善款的使用,一般遵循专款专用,由善主“亲募亲散”,但在特殊情况之下,可以更改善金的用途,“权为变通移济,不致拘泥偏枯,名称其实”。 到了光绪初年,制度建设逐步走入正轨,善堂资金来源充沛。善堂建设更为完备,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堂内首事增加到四人,各负其责。一人负责“支派各务”,并“察核项目”。一人管理银钱,经收租息。一人执掌契据,经理支发。一人督办各项善举,稽查全堂事务。四人分头承担,既能免“独力难支”,也能防止“久专生弊”,互相监督。以上四人各专责成,一年一换。同时,首事每月朔望各集议一次。 其次,堂内增加董理一人,“兼管襄办各务,觉查各项善举”,也就是具体负责经理堂内的日常事务。由在堂多年,熟悉堂内事务的人充当,特别是要对药材比较熟悉。 第三,堂内又增加管帐、看司、帮办等人员六人。看司一人职责限于经手各种租息、照管堂内存用器物并传知单;帮办一人专职负责香等照料、药材购进等事;片药一人负责经理药室。同时,对清水溪善庄建设也制度化了。该庄办事人员额设七人。其中帐务一人,负责经理善庄各务,登挂流水帐目并催收租息;花匠一人,负责培养善庄花木;看司一人,经理香灯照应,并打扫卫生。打杂二人,负责善庄的菜园经理;教习一人,火夫一人。 第四,受巴县县令的委托,托管保节堂。保节堂系巴县“公款善举”,也就是政府拨款兴建起来的,后因管理不善,善行逐渐荒废,收养的孀妇数目仅74名,原有善款也有被侵吞的危险。由至善堂代管后,保节堂的堂务管理走上正途。光绪十年,巴县地方政府又将养济院委托至善堂首事管理。 第五,于光绪七年()增办全节堂,收养未满三十,贫苦无依而又愿意守节的节妇。因为保节堂经费有限,孀妇收养数目有限,完全不适应当时的发展情况,设立全节堂,增加收养孀妇的名额,人数在52名左右。 三、至善堂的善行 作为清代巴县第一大善堂,至善堂的善行经历了一个逐步扩大、完善的过程。其善行的对象,既有八省会馆的后裔子孙,也有大量地方普通民众,这让至善堂逐步具有社区慈善机构的性质。 咸丰九年(),至善堂刚成立时,订立善事十三条,规定了该堂善行的运作方向。以救济的对象不同,笔者分为三大类进行归类说明。 首先,善行的主要对象是八省会馆民众及其后裔。如设立义学,善堂每年招收会内民众子弟三十人入学,并给主讲者束脩钱三十四千文。又如对义地的管理,不许“花葬以紊条规”。至善堂义地由堂内首士蒙应志堂所买白冤堂田土,该地位于孝□□甲,土名海棠溪石家嘴内牌坊岗、相子堡二处田土二段,捐舍入至善堂内,永远作为义冢,平日由佃户照管。需要在义地埋葬的,不论贫富、远近,先到堂内区的票号,按序埋葬,不得抢占棺位。 其次,善行的对象虽然包含有八省会馆的后裔,但主要的受惠者来自于巴县地方社会的普通民众,救济对象突破了“省籍”限制。这类善行包括下述几类。 第一,宣扬儒家意识形态。包括“兴崇宣讲”,每逢朔望,至善堂请人宣讲圣谕;散发善书,将各善士送来的格言劝善等书转发给一般民众,“随收随送”;收捡字纸,每人每月给工食钱一千四百文,按月支发。 第二,医疗救治。包括设立义馆,春夏季节,请医生两位,秋冬病少,减请一位,坐堂行医;送施方药,每年募集方药,发放给“贫苦无力取药者”。 第三,针对特殊人群的救济。包括以下几类: 1、救育女婴。巴县地方社会中如有贫苦人家女婴,验明正身后,每月每名给钱五百文,以三月为限,送入育婴堂收养。 2、“养瞽目”,也就是收养照料盲人。“天下之最堪悯者,莫瞽者若也”。至善堂在清水溪专门设置养瞽院,额定收养盲人五十名,进院的盲人,需要有人担保。同时,养瞽院聘请老师二人,教盲人一些简单的维持生活的技能,“或教以醒世之歌词,或教以推人之算法”,亦即所谓的唱圣谕和算命。为此,养瞽院将入院的盲人分为两班,格言班和命理班。格言班三个月一班,命理班八个月一班。学习期满后,即自谋衣食,不许久住在院。从材料来看,光绪三十四年,共收养盲人30名,从籍贯来看,巴县6人,重庆府(巴县以外)22人,四川省(重庆府以外)1人,外省1人。年,共收养盲人29名,其中籍贯不名的6人,本县2人,本府(除巴县外)13人,其他县6人。 3、冬春之际救济地方社会的穷苦民众。作为长江上游最大的水码头,巴县的外来穷苦民众众多。每年秋冬之季在朝天、金紫、临江等地开办粥厂,散发棉衣,所需经费由八省客长向城内各商募捐。 最后,善行对象就是以社区民众为主,这让至善堂具有了社区慈善机构的色彩。如施给茶水,每年夏秋季在交通要道设立送水点,免费发送茶水。又如施送棺板,掩埋无主尸首。至善堂在城内储奇、朝天、华光、南纪四坊,城外金紫、临江、太平四厢等地设立棺板施送处,雇人掩埋巴县城区的无主尸首。同治五年(),至善堂还在广阳坝设立收尸处,本着“救人不救货”的原则,制定救生捡尸规则:船户自水中捞救活生一人,给钱五百文;若是在船上救的(救人者未下水),给钱三百文。但救一人,最多只给一千五百文,若多人参与施救,均分救济金;救生时,只许救人,不许捞物;捞取一具浮尸,给钱一百八十文,抬埋者,每棺给钱二百六十文。同时,埋葬的尸体要标明年月、序号,以待尸亲寻认。为了防止弊端,至善堂在船户中选一人充做头目,每年给工资钱二千文,负责监察实施上述规定。所选之头目,每年更换。 综上所述,至善堂的施善对象已经超越了个人籍贯,主要以社区救助为主,不管移民也好,土著也罢,都在他们的救济范围之内。至善堂已突破了传统的畛域,将目光转向追求“整个社会和全体市民的利益与福祉”。这种转向的内在动力,在于掌握至善堂的八省客长已经处于巴县城区权势网络的核心。通过多项救济活动,也反过来巩固了八省客长的核心地位。这是一个相互作用与反作用的过程。 四、至善堂财务收支 至善堂每年的收入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堂内原有田房产业的租息、当商利息。如所代管的保节堂,光绪初年每年的田地的租谷、房屋的租金大约有一千七百余两。 另外一部分就是每年的捐款收入。这笔钱的数量相对来说,更为庞大。清代的相关数据笔者尚未找到,我们以民国十年()至善堂的各类善款、善物的会计表来看这年至善堂的一些运行情况,请看下表。 表五年至善堂所收捐款、捐物情况汇总表 名目 施主数量 捐献数量 施药材 家药铺 共施济药副 济药罐 7家药铺 个 书 2人次 40部 棺板 79家商铺(或个人) 副 济米 30家商铺(或个人) .69石 棉衣 1人次 件 捐款 63家商铺(或个人) 文 资料来源:民国《巴县县署》档案-1-《至善堂材料汇编》。 从上表可以看到,至善堂善款收入及捐物来源比较多元,就拿每年一次的药材、书籍、大米、棉衣、棺材捐献来说,巴县城内几乎所有的店铺都参与其中。从这个表中,有几个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 第一是参与捐款、捐物的店铺、商家数量众多。这反映出晚清至民国时期,至善堂的影响力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移民商人这一狭隘的群体之中,已成为巴县甚至重庆救济活动的中心之一。 第二是参与捐款、捐物的药铺、商家或个人所捐的数量都不是很大,如泰安号捐了茯苓八斤、永兴行捐米六斗,商家并没有因为捐献而对自己的商业发展造成多大的困难。 从第一点来看,这可能反映了两个事实,一是当时的商铺对善事的参与热情比较高昂,而另外一个事实则是至善堂在众多的商家中有着较为良好的信誉或号召力,当时的重庆善堂众多,各个善堂为了能够继续生存下去,都在向商家募捐,至善堂能够在其中吸纳比其他善堂多出几倍、几十倍的善款,显然与它的领导层在地方社会的人脉有关。换言之,八省客长在背后的支持是至善堂成功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就第二点来说,虽然各家商铺所捐数量不多,但因为参与捐献的商铺的数量众多,积少成多,当年总的善款、善物就不少,如这年就发出济药副。 至善堂还有一项重要的善事是在游民较多的朝天门码头等地开办粥厂,救济衣食无着的贫民。这项救济活动始于每年中秋节后,八省会馆值月首事即按照捐簿向各商铺善士收缴粥厂经费。《巴县档案》中保留有同治五年巴县善主捐款的名录,兹引如下。 表六同治五年粥厂捐款名录 捐主 款额 捐主 款额 官盐店 每年捐银四百两正 六当 每年共捐银二百两正 三里 各捐银三百两正 城内二十三坊 共捐七百三十两 洪豫章 每年捐银一百两正 闽聚福 每年捐银一百两正 晋安泰 每年捐银一百两正 江安 每年捐银一百两正 楚宝善 每年捐银一百两正 关允中 每年捐银一百两正 宁兴安 每年捐银一百两正 广业堂 空 城外十厢 每年共捐银二百两 职员金含章、鲍崇礼 厂费营六百两 资料来源:巴县档案6-5- 在上表中,洪豫章、闽聚福、晋安泰、江安、楚宝善、关允中、宁兴安、广业堂为八省客长成员,金含章也担任过八省客长。可见,八省客长所出的资金占了粥厂捐款近一半。善堂的支出情况,编于民国十年的《至善堂材料汇编》对该堂每月的一个支出情况进行了一个简单的统计。 表七民国十年至善堂每月支出款项细目表 名目 数额 银 钱 小学堂 一十四两二钱 一十六千八百文 蒙学二所 一十四两 医馆 一十四两二钱 八千文 全节堂住堂节妇及子女 五十八两二钱 散居孀妇 一十两 四十千文 孤老 —— 三十五千文 瞽目 —— 四十千文 办事教师夫役 —— 五十九千文 总共 一百一十两零六钱 一百九十八千八百文 资料来源:民国《巴县县署》档案-1-《至善堂材料汇编》 上述款项只是例行的每月要支出的银钱数目,每年总数大概在银二千六百余两、钱二千四百余千文左右。同时还有许多临时性的支出,如香灯修理、祭祀、酒席、添置器具及学堂杂用等的费用支出,每年大概在五百余两左右。总体来说,每年“岁入租金息金约一万三千元,岁支约一万五千余元” 但总的来说,大部分年岁的收支相抵,都会略有赢余。如光绪十八年(),当年就赢余银一百两零一分,钱七百二十六文。又如宣统元年,代管的保节堂收支相抵后就余银五十七两五钱六分。 至善堂能够取得良好的运营效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经理首事的热心负责。当时他们在选定首事时就要求首董者“尽心协力、公而忘私”。籍贯湖北的罗学钊曾在光绪三十四年()充任过该堂的首事,该年农历五月十六日,他在日记中说,今天轮他到石桥场负责办理救济婴儿的事情,当天天气不好,赤日当天,暑气逼人。家中人都劝他人年老了,经不起这么热的天气,劝他当天不要去了。他在日记中说:“予办公以来,未有不到之班,亦未尝怀畏寒畏暑之念。特将劳动歌词示谕家人。”最终还是上路办公去了。 如同巴县的其他公款一样,这些善款在清财政困局的大背景下,经常被挪做他用。光绪八年(2),巴县李知县因公提用保节堂本银七千四百两,在保节堂首事金德均的屡次要求下,才答应分多次偿还。又如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罗学钊在他的日记中说,九门负(附)郭,“沿河两岸,隆冬之际,贫民饥寒交迫。昔有粥厂,赖此以延残喘者不少。惜当道将此项提作别款”,表达了他对地方官员擅自挪用善款的不满。 宫保利在分析清代后期苏州地区的公所善举活动时,认为这些善堂的经费主要由同业各商号捐赠及抽厘。换言之,宫氏认为,苏州地区由行会公所举办的善堂的经费主要来自于各行会公所。而从至善堂的经费来源看,虽然它的领导层由八省会馆的首事来担任,但这并不影响到它的经费来源的多元性。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至善堂的善款来源非常多元性和普遍性,完全摆脱了会馆自身的桎梏。 五结论 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八省会馆是清代重庆地方社会中最为强大的移民组织,自咸丰以后在地方权力结构中扮演着核心的作用。但因其“外省籍”的身份,八省会馆在地域社会中与本地士绅粮民存在着竞争的关系,地方士绅往往指责八省客商不为地方社会的安危和发展负责,而只顾自己赚钱。为了回击本地士绅的指责,同时也为了八省会馆内部的自我救济,彰显其服务同乡的责任,由八省会馆创办的至善堂走上了历史的前台。 从至善堂的管理与运行来看,也起到了扮演八省客商与地方社会的中介作用。从至善堂的管理、经费来源来看,八省会馆都起到了主导的作用。其经费主要是来自于最初八省会馆捐款所购置的田产、地产的租金收入。而从至善堂的善行来看,其救济、资助的范围则已超越了移民的团体,而包括巴县各省籍在内的民众,从而成为社区救助的中心。这一资助与受助群体分离的现象正是反映了八省会馆试图通过至善堂进入社区权力网络内部的努力。而到晚清时期,我们发现,至善堂的资金来源包括越来越多的本地店铺、民众。这说明至善堂的管理和善行已经得到社区民众的认可。这反映了至善堂的影响力已逐步从移民群体转向整个巴县,从而进入到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之中。 (摘自吴佩林、蔡东洲主编:《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版,第—页。) 圖Gethin赞赏 长按白癜风专家问诊百姓放心北京哪个专家治疗白癜风好
|
当前位置: 江安县 >梁勇周興豔移民善堂與地方權力結構
时间:2018/9/11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全面落实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江安怎样做
- 下一篇文章: 弘扬环保精神,彰显新江安美好形象直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